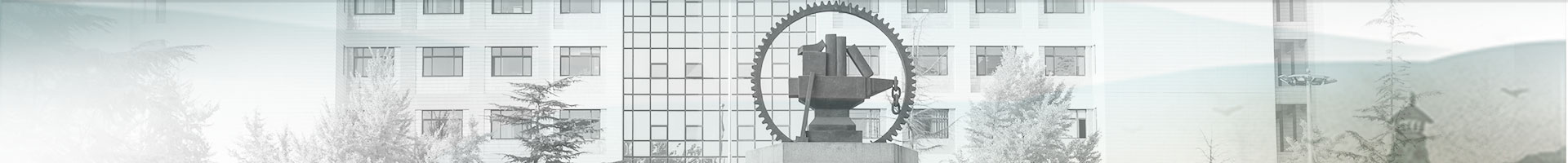
對(duì)于中國(guó)的資本市場(chǎng)而言,剛剛過(guò)去的2014年無(wú)疑還是以并購(gòu)為主題的一年。順理成章地,《并購(gòu)之王——投行老狐貍深度披露企業(yè)并購(gòu)內(nèi)幕》這本書(shū)就在亞馬遜網(wǎng)店登上了經(jīng)濟(jì)管理類中“企業(yè)并購(gòu)與重組”類書(shū)籍銷量的第1位。
然而,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有趣的現(xiàn)象: 我身邊的很多投行人在購(gòu)買并閱讀這本書(shū)之后都覺(jué)得不以為然。普遍的看法是有些乏味,甚至看不太懂。有位投行人士的評(píng)論很具有代表性,他說(shuō):“花了兩個(gè)星期看完這本書(shū),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書(shū)名都好浮夸啊!”
無(wú)疑,相當(dāng)一部分在國(guó)內(nèi)從事并購(gòu)交易的人認(rèn)為這本書(shū)的內(nèi)容并沒(méi)有書(shū)名那么震撼,他們很難在書(shū)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并購(gòu)知識(shí)。
然而,我在閱讀這本書(shū)之后卻發(fā)覺(jué)難以抑制我內(nèi)心的激動(dòng):如果我能提早一年關(guān)注到這本書(shū),那么我在海外并購(gòu)的財(cái)務(wù)顧問(wèn)業(yè)務(wù)中可能會(huì)少走許多彎路。
為什么我與我的一些投行朋友對(duì)這本書(shū)的評(píng)價(jià)會(huì)如此迥異?
其實(shí)答案已經(jīng)非常明顯:這本書(shū)所講述的,是美國(guó)成熟市場(chǎng)的并購(gòu)規(guī)則和經(jīng)驗(yàn),已經(jīng)超越了目前A股的并購(gòu)發(fā)展階段。
當(dāng)發(fā)達(dá)國(guó)家已進(jìn)入并購(gòu)4.0時(shí)代,我們其實(shí)還停留在2.0時(shí)代。這絕非妄自菲薄,無(wú)論從并購(gòu)的動(dòng)機(jī)或是并購(gòu)的游戲規(guī)則來(lái)看,中國(guó)市場(chǎng)上的并購(gòu)還是自成一派的玩法:
首先,大多數(shù)中國(guó)資本市場(chǎng)上并購(gòu)的發(fā)生不是出于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的清晰考量。很多公司為了并購(gòu)而并購(gòu),不是把并購(gòu)當(dāng)作企業(yè)發(fā)展的工具,認(rèn)為并購(gòu)本身就是目的。
經(jīng)歷了2013年、2014年兩年中國(guó)資本市場(chǎng)“全民并購(gòu)”的熱潮以及媒體狂轟濫炸式的宣傳,如今,幾乎每個(gè)人都耳熟能詳?shù)氖牵喝蛞呀?jīng)歷了五次并購(gòu)浪潮——有學(xué)術(shù)文章稱準(zhǔn)確的說(shuō)法是美國(guó)經(jīng)歷了五次并購(gòu)浪潮,當(dāng)然,美國(guó)是整個(gè)世界上并購(gòu)交易最發(fā)達(dá)的國(guó)家。
這五次并購(gòu)浪潮各有特點(diǎn):第一次并購(gòu)浪潮(1893年-1908年)以橫向并購(gòu)為主;第二次并購(gòu)浪潮(1919年-1929年)以縱向并購(gòu)為主;第三次浪潮(1955年-1969年)呈現(xiàn)出混合并購(gòu)的特點(diǎn),形成了一些綜合產(chǎn)業(yè)帝國(guó);第四次浪潮(1974年-1989年),則是杠桿收購(gòu)和敵意收購(gòu)為主;第五次并購(gòu)浪潮(1993年-2000年)以全球化為主要驅(qū)動(dòng)因素之一,信息技術(shù)、金融等服務(wù)行業(yè)成為并購(gòu)的重點(diǎn)。
如果我們以此來(lái)對(duì)標(biāo)中國(guó)資本市場(chǎng)上這兩年間密集發(fā)生的并購(gòu),我們很難梳理出這樣清晰的并購(gòu)思路,很多并購(gòu)交易的發(fā)生,既不是橫向的也不是縱向的,卻呈現(xiàn)出奇特的“跨界”思路——縫褲子的想成為電商,做撲克的進(jìn)軍醫(yī)藥行業(yè),賣煙花的要去做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而做木材家具的看上了游戲行業(yè)。
還有許多并購(gòu)旨在迎合當(dāng)下最流行的互聯(lián)網(wǎng)概念,不同行業(yè)的企業(yè)紛紛去并購(gòu)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給上市公司注入網(wǎng)絡(luò)概念,卻全然不顧是否有能力整合這些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比如零售行業(yè)的銷售收入受到網(wǎng)店的沖擊非常大,于是不少公司考慮去并購(gòu)一家電商,給公司注入互聯(lián)網(wǎng)概念。然而并購(gòu)是一項(xiàng)高成本高風(fēng)險(xiǎn)的資本運(yùn)作,如果為了刺激銷量,在天貓等主流電商上面開(kāi)網(wǎng)店、做營(yíng)銷,所需的投入更少,但對(duì)銷售收入的刺激未必比并購(gòu)一家電商要小。
其次,我們遵循的并購(gòu)市場(chǎng)規(guī)則與全球并購(gòu)的市場(chǎng)規(guī)則不接軌,我們的并購(gòu)估值體系并不完善。
比如在海外并購(gòu)中經(jīng)常提到的EBITDA(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rùn))概念,在中國(guó)的并購(gòu)市場(chǎng)中幾乎用不到,很多投行人士和企業(yè)家們也都不熟悉。
我記得自己曾經(jīng)帶一位企業(yè)家去東京與國(guó)際知名的PE機(jī)構(gòu)談判并購(gòu)一家日本企業(yè)的事情。在正式談判以前,我們拿著財(cái)務(wù)報(bào)表與企業(yè)家討論談判的內(nèi)容和策略。他對(duì)業(yè)務(wù)和商業(yè)運(yùn)營(yíng)有非常了不起的見(jiàn)解,但在看財(cái)務(wù)報(bào)表的時(shí)候卻有很多疑惑,最核心的問(wèn)題就是:什么是EBITDA?為什么要用EBITDA估值?
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最簡(jiǎn)單的解釋是:EBITDA反映了一間公司最核心的能力——現(xiàn)金創(chuàng)造能力和業(yè)務(wù)盈利能力。
EBITDA代表的是企業(yè)的現(xiàn)金流。在杠桿收購(gòu)的時(shí)代,收購(gòu)方考量一間公司的EBITDA,實(shí)際上也是評(píng)估一家公司的償債能力。此外,不同國(guó)家的稅率、利率、折舊攤銷政策又各不相同,如果對(duì)凈利潤(rùn)進(jìn)行比較(用P/E估值),很難對(duì)不同國(guó)家之間企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能力有一個(gè)客觀的判斷。用EBITDA作為估值基礎(chǔ),排除了不同行業(yè)和不同企業(yè)之間的資本結(jié)構(gòu)、稅收政策的影響,專注于其業(yè)務(wù)盈利能力的判斷。
在《并購(gòu)之王》中,對(duì)EV/EBITDA估值和P/E估值的不同,有了一個(gè)清晰的闡釋。作者指出,EBITDA估值以稅前利潤(rùn)為基礎(chǔ),是針對(duì)未上市的私人企業(yè)的估值方法,而P/E估值則以稅后凈利潤(rùn)為基礎(chǔ),可以用來(lái)評(píng)估上市公司。但P/E比率僅僅是由上市公司股東買賣股票這一集體買賣行為實(shí)時(shí)決定的,它只反映了股權(quán)價(jià)值(市值),而沒(méi)有反映整個(gè)企業(yè)的價(jià)值。
中國(guó)的投資者,無(wú)論是在購(gòu)買一間上市公司還是投資一間非上市公司,都只采用P/E估值方法,忽略了購(gòu)買一間企業(yè)所需要承接的負(fù)債,以及企業(yè)資產(chǎn)負(fù)債表上現(xiàn)金部分的價(jià)值。然而在中國(guó)企業(yè)走出去趨勢(shì)愈加明顯的今天,了解EBITDA估值方法已經(jīng)成為必須的一門功課。
如果《并購(gòu)之王》真是一本超越了A股并購(gòu)發(fā)展階段的書(shū),我們?yōu)槭裁催€需要讀它呢?這是立足當(dāng)下又如何備戰(zhàn)未來(lái)的邏輯。
我們已生活在一個(gè)10倍速的時(shí)代,這意味著成功與失敗都以10倍速進(jìn)行,前瞻性已經(jīng)成了這個(gè)時(shí)代生存下來(lái)必不可少的技能之一。雖然發(fā)生在中國(guó)資本市場(chǎng)上的并購(gòu)交易還不能與成熟市場(chǎng)等量齊觀,但目前國(guó)際化接軌的趨勢(shì)已經(jīng)非常明顯。
2014年,證監(jiān)會(huì)大幅度放開(kāi)了企業(yè)并購(gòu)重組相關(guān)的審核機(jī)制,并且對(duì)原有的若干規(guī)則都做了市場(chǎng)化的修訂,游戲規(guī)則正在逐步向成熟市場(chǎng)靠攏。此外,大量的中國(guó)企業(yè)出海并購(gòu),這些企業(yè)都必須在跨出國(guó)門的過(guò)程中學(xué)習(xí)成熟市場(chǎng)的規(guī)則,才有可能完成并購(gòu)、做好并購(gòu)。也許有企業(yè)在不研究如何進(jìn)行估值的情況下也完成了交易,但無(wú)疑是多付了學(xué)費(fèi),成果如何也是未知。
《并購(gòu)之王》里關(guān)于并購(gòu)的精髓最重要的兩條是:正確全面的估值方法和交易撮合技巧。這是未來(lái)投資銀行家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的核心技巧,也是市場(chǎng)走向成熟之后投行在并購(gòu)交易中的核心價(jià)值。
關(guān)于估值的方法,是“實(shí)際交易的藝術(shù)性和正式價(jià)值評(píng)估的科學(xué)性”的結(jié)合,就像是坐在蹺蹺板兩端的兄弟。本書(shū)開(kāi)篇引用的奧斯卡·王爾德的一句話即指出了估值的重要意義:“有些人知道所有東西的價(jià)格,但關(guān)于價(jià)值卻一無(wú)所知。”一次成功的并購(gòu)不僅僅是買到一間好的公司,更重要的是以便宜的價(jià)格買到它。
刻板地套用估值模型很可能會(huì)出現(xiàn)明顯的錯(cuò)誤,因?yàn)楫?dāng)人們太過(guò)關(guān)注定量估值時(shí)(用數(shù)學(xué)來(lái)估值),就往往會(huì)忽略了定性估值——從一個(gè)企業(yè)未來(lái)的利潤(rùn)穩(wěn)定性和盈利機(jī)會(huì)出發(fā)來(lái)考量的并購(gòu)價(jià)值驅(qū)動(dòng)因素。此外,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每間公司的特殊性都會(huì)影響估值模型當(dāng)中假設(shè)的建立,不同的收購(gòu)主體也會(huì)有不同的并購(gòu)協(xié)同效應(yīng)。但估值當(dāng)中最容易犯的錯(cuò)誤又是對(duì)潛在的協(xié)同效應(yīng)估計(jì)過(guò)高。
能夠綜合上述種種而給出一個(gè)合理的估值,要求專業(yè)的投行人士給出建議。而一個(gè)顯而易見(jiàn)的問(wèn)題是,目前中國(guó)的投行在并購(gòu)交易的估值方面,發(fā)揮的作用太少。
此外,撮合交易的技巧也決定了并購(gòu)交易的成功率。本書(shū)最富趣味性的部分,同時(shí)也是貫穿全書(shū)的部分,就是有關(guān)撮合交易中的各種場(chǎng)景故事重現(xiàn)。每一章的案例故事都揭示了一個(gè)并購(gòu)交易撮合的難題:玩世不恭的企業(yè)家,老謀深算的對(duì)方顧問(wèn),不夠?qū)I(yè)的中介機(jī)構(gòu)……出現(xiàn)最多的還是不懂并購(gòu)藝術(shù)的客戶,而作者的目的是告訴讀者如何技巧性地解決各種難題或者放棄不靠譜的并購(gòu)交易。如果你不愿意了解那些目前在中國(guó)市場(chǎng)上暫時(shí)還用不到的交易技術(shù)細(xì)節(jié),至少可以耐心讀完每一章的故事案例,人性實(shí)際上是相通的,那些案例中活靈活現(xiàn)的表現(xiàn),也是我在中國(guó)企業(yè)家身上經(jīng)常見(jiàn)到的。
本書(shū)的第30章花了相當(dāng)長(zhǎng)的篇幅告訴投資銀行家和咨詢顧問(wèn)如何從事并購(gòu)交易的財(cái)務(wù)顧問(wèn)工作,作者指出了成功的投行顧問(wèn)的幾個(gè)特點(diǎn):喜歡與人打交道,喜歡各種各樣的事物,擁有高抗風(fēng)險(xiǎn)能力。同時(shí),要把一半以上的工作時(shí)間花在市場(chǎng)營(yíng)銷和業(yè)務(wù)拓展上。當(dāng)中國(guó)的投行人員還在抱怨并購(gòu)業(yè)務(wù)成功率太低的時(shí)候,應(yīng)該思考:我們究竟花了多少時(shí)間在業(yè)務(wù)拓展和專業(yè)研究上?
隨著家族企業(yè)的二代繼承意愿下降,以及技術(shù)更新加速導(dǎo)致的企業(yè)生命周期縮短,未來(lái)的并購(gòu)交易會(huì)越來(lái)越頻繁,并購(gòu)將成為企業(yè)發(fā)展路徑上的常態(tài)。未來(lái)這一領(lǐng)域的市場(chǎng)空間將會(huì)非常大。也許今天中國(guó)資本市場(chǎng)上那些投機(jī)心理強(qiáng)烈的并購(gòu)明天會(huì)成為一地雞毛,但并購(gòu)的浪潮不會(huì)停止。作者認(rèn)為中國(guó)將是未來(lái)并購(gòu)市場(chǎng)的主體——因?yàn)椴痪玫奈磥?lái),中國(guó)會(huì)成為世界上主要的金融強(qiáng)國(guó)和世界上最大的講英語(yǔ)的國(guó)家。我毫不懷疑,下一個(gè)二十年的并購(gòu)之王會(huì)誕生在中國(guó)。
投資中國(guó)網(wǎng) 2015年01月05日